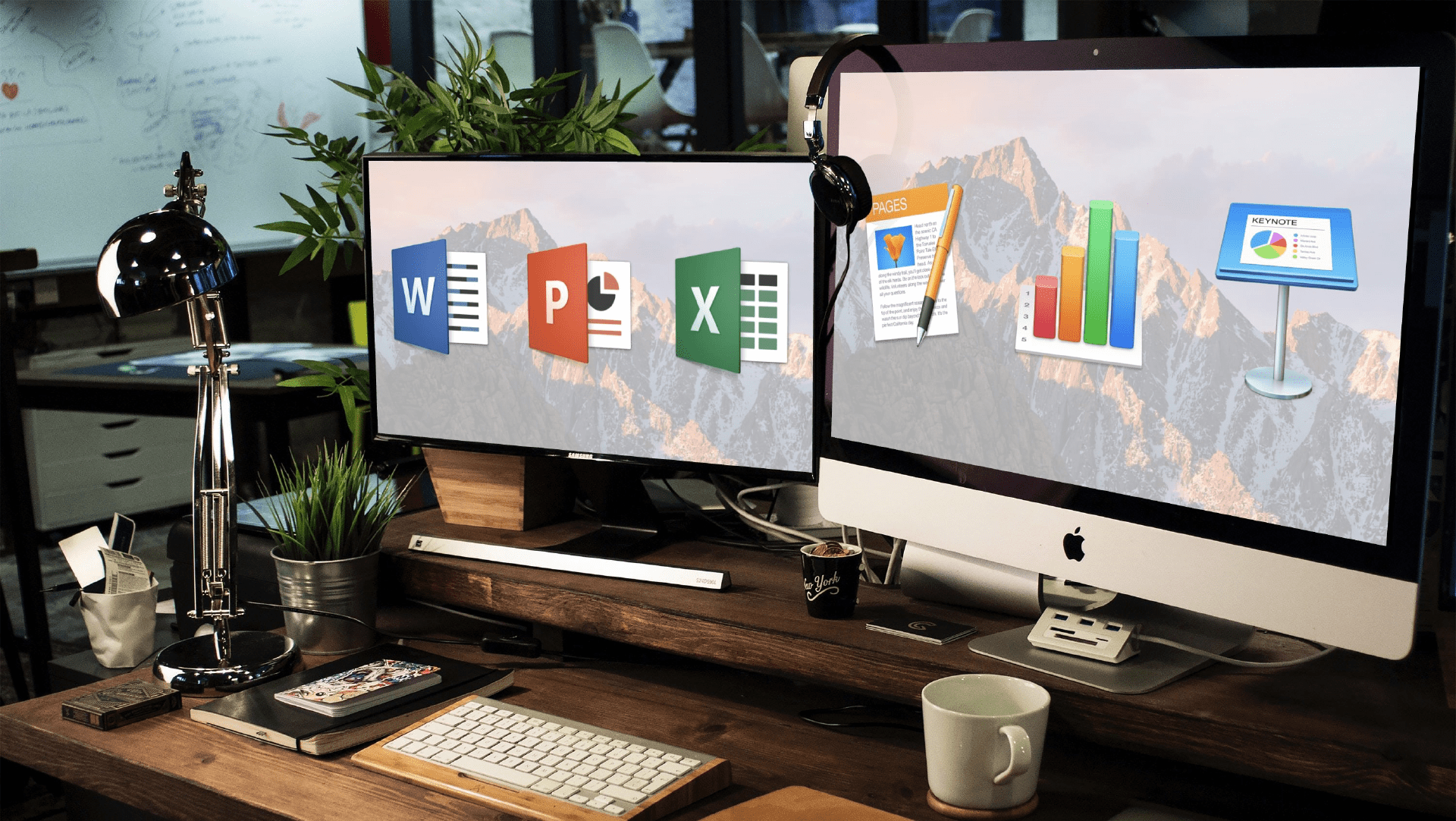边民初进学堂(看60版的人如何上学)
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,学生全国大串联,学校停课闹革命。
边疆有边疆的好处,老百姓还是认为孩子必须送进学校,否则通通变成小野人怎得了?再说了,父母哪有时间照顾我们?太阳没出山,他们就上山砍伐森林开挖梯田,太阳落山,一把火点燃几天前砍伐在地枯萎干燥的大树小草,一座山一座山烧得通红,这才荷着砍刀锄头回家。
在父母眼里,孩子进学校也就是进了“公办保姆院”了。
法定年龄是7岁上小学,这不,文化大革命了,毛 最高指示说了:学制要缩短,教育要革命。五岁的边民混进了学校。
课本是红彤彤的“红宝书”——一本《老三篇》一本《毛 语录》,都是毛 著作。三十多年过去,我仍能大段大段背诵那些课文,特别是林彪副统帅的“再版前言”:毛/泽/东/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,他继承捍卫和发展了……
不背诵毛 语录不仅是个学习问题,更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。比如你去吃米线,先得背毛 语录:“毛 教导我们说,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,给我来碗五分钱的米线。”卖米线的也得说:“毛 语录,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,拿着,你的米线。”
买卖双方若有一方不背诵毛 语录或者背错了,麻烦就大了,交易自然是立即取消,现场全体人员还立刻组织起一场批判会,对你进行“触及灵魂深处的革命”,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。
每天早上,广播喇叭播放《东方红》,大人小孩一律得到操场上背诵毛 语录,叫做“早请示”,然后开始随着《敬爱的毛 》音乐跳“忠字舞”,也就是后来学校里的“广播体操”了。每天晚上,“忠字舞”少不得再跳一次,结束曲换成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,这叫“晚汇报”。目的都是为了“向毛 党中央表忠心”。
半夜三更,毛 在中南海说了一句话,全国就得起床迎接和庆祝“最高指示发表”,敲锣打鼓大肆热闹一番。交响曲《北京喜讯到边寨》我一听就犯晕,半夜听到,会立即揉着眼屎从床上爬起来去操场集合,不是不好听,条件反射啊。某地还是某国,给毛 送去几只芒果,老人家吃了连连说好,这还得了?芒果顿时身价百倍,成了“果王”,搞得我们这些爬树乱摘芒果的小屁孩一上树就双腿打抖。中国产芒果的地方特少,大部分地方便塑了芒果的塑像加以供奉,70年代80年代我去很多地方旅行,还看到过不少的“芒果”神像。
有次,毛 填词,内有“不须放屁”一句,我们这些小屁孩就整天尾随着有放屁嫌疑的人,只要听得一声响从胯间发出,冲将上去,双手合十,对着人家屁眼就是恶狠狠用劲一插,高叫着“毛 教导我们说——不须放屁!”被插的人肛门痉挛连锁反应至胃痉挛,极其难受,却又作声不得,脸色阴晴不定。谁敢违背毛 语录?那是杀头的罪,叫做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。我记得那是童年最流行的一种娱乐项目,很有防治痔疮的功效。
边民虽是同级学生中年龄最小的,背“红宝书”可是一点都不含糊,甚至还操练过倒着背,验证“倒背如流”的可行性。跳“忠字舞”幼稚可笑,但一派天真烂漫,深受老师和大人喜欢。很快,学校就慧眼识珠将边民选进“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”,唱唱跳跳到处演出。印象中,扮演过微型版的“小炉匠栾平”“参谋长刁德一”等等,至于演过什么“正面英雄人物”反而不记得了。这记忆吧,大约跟性格有关,演反派记得牢,那是因为坏人好玩,喝酒吃肉调戏妇女,很人性,下场虽然难免不得好死,毕竟快活过日。用毛 语录来说就是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”(他老人家也是引用太史公的话)。我还是觉得“鸿毛”潇洒飘逸,人生如梦,如鸿毛,多贴切。死成泰山那样,没劲,我登过,平原上一个小山包而已,看不出哪里好玩,还联想到左冷禅,越发不乐意。
背“红宝书”远不能满足求知欲,太简单。便去找高年级的师兄们“跳岛战役”式学新鲜东西。老师教着加减法,我已经把乘法口诀背得滚瓜烂熟,除法表也刻在脑子里。一年级读完,跳级,直接读三年级,坐在第一排座位,身后同学个个比我高出一个头以上。受欺负啊,师兄师姐都来脑壳上凿爆栗掐脸蛋,不用化装,直接就可以上台演“花脸”。同学都比我大三岁以上,那是什么概念?他们九岁才读三年级,边民六岁就读了,这就惹了众怒,是可忍孰不可忍?刻骨铭心的是一个师兄经年累月欺负我,他是班里的霸王,直到成年,我见了他面从不理睬,三十年不跟他说任何一句话。大概他早忘了童年,到处问别人:他怎么不理我呢?这师兄在工商局当点小官,那些年听说我做生意,乐呵呵地拉着税务局弟兄主动来帮忙:要什么执照,发票?我派人给你送来。我一言不发,烟都不递一根,目无表情。不知道他现在想通了没有。
父母带领一队“知青”转移到新的原始森林开荒种橡胶,我也不得不转学了。
新的学校象个“草台班”,教室是茅草棚,竹篱墙,四面透风。天上下大雨,教室里下小雨。全校老师只有两名,一个教语文一个教算术,包教一年级到五年级,后来知道这叫“复式教学”,其实是没办法的办法。
从家里去上学,走的是弯弯曲曲小道,穿森林河流,翻几座山。天蒙蒙亮上路,太阳当顶才进入教室。冬天比较惨,没鞋子穿,赤脚走山路,露水、寒气、荆棘之下,一双脚地图似的纵横交叉布满裂口。用铁皮罐头空盒钉穿些小洞,装进火炭,拎着去上学,一路走一路甩炉子,怕碳火熄灭。走一段停下来烤烤脚板,拔拔刺,舒服之际,高歌一曲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,自我感觉红小兵跟小红军没啥两样。读到初中,开始有鞋子穿,布鞋,一双脚有了归宿,百感交集:有鞋子穿,真幸福,社会主义就是好来就是好,什么时候亚非拉苦难人民也象我一样有鞋穿有学上,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吧?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骨肉同胞,也能象我一样吃上包谷饭,那就是解放了。
一生中,最快乐幸福的学生生活,应该就是这几年“草台班”学校中度过的了。
教语文的北京女知青王老师是我一生最爱的老师,人漂亮,普通话标准,讲故事一流。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子野先生爱女,高干子女,藏有那年代许多“禁书”,常常拿出来讲给我们这些半懂不懂的小孩听。王老师后来读大学学的是什么“西班牙语”,怪乎哉,她的汉语那么好,干吗要去学拉丁语系?让我始终想不通。
教算术的张老师是上海女知青,娇滴滴的,用上海话说,有些“发嗲”。难怪后来我的数学一塌糊涂,大约是被张老师“嗲”糊涂了。但她是好人呐,关心学生无微不至,温柔、母性、善良这些东西,在她身上表现得很淋漓。12岁我流浪到上海混了大半年,得到许多张老师一样的大姐阿姨的照顾,终身感激,爱极了上海女人。
读到五年级,老师生病的生病,回家探亲的探亲,学校只好放长假。来年重开学,再读五年级,等于读两次五年级,跳级也白跳了,重归本位。要不,14岁就该高中毕业去读大学的,耽搁了一年,人生就有了另外的不同,此是后话。